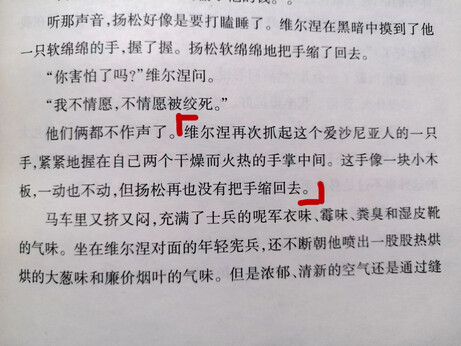蒔岡雪子 · @Haruko
359 followers · 4320 posts · Server donotban.com“它要倒塌啦!”我叫喊起来,“弟兄们,它要倒塌啦!”
“你在瞎说,麻风病人。”弟兄们对我说。
这时,我就请求弟兄们说:
“就算它不倒,难道每一具尸体不就是登上墙顶的一级阶梯吗?我们人很多,我们的生活都痛苦得不堪忍受。就让我们用尸体铺遍大地吧;在尸体上再堆上新的尸体,这样,我们就可以登上墙顶了。到那个时候,哪怕只剩下一个人——至少也可以有一个人看到新世界了。”
我满怀愉快的希望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背脊,冷漠、肥胖、倦怠的背脊。那四个人仍然忽而拥到一起,忽而又分开,旋转着,无休无止地跳着舞;黑沉沉的夜仍然像个患病的女人,不断地喷吐出湿淋淋的砂粒;那墙仍然是一座不可摧毁的庞然大物,照旧耸立着。
“弟兄们!”我请求说,“弟兄们!”
但是我说话时带着很难听的鼻音,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谁也不愿听我这个麻风病人讲话。
灾难啊!……灾难啊!……灾难!……
蒔岡雪子 · @Haruko
359 followers · 4320 posts · Server donotban.com人群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紧接着一个走了出来。他们摩拳擦掌,坚定地、不可动摇地提出痛苦的要求:
“还我孩子!”
这时,我这个麻风病人也终于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力量和勇气。于是,我走到前头,大声地威胁着叫喊道:
“杀人犯!把我还给我自己!”
而这堵墙呢——这堵墙依旧沉默着。它竟是这么虚伪,这么卑鄙,居然装着全没有听见,于是我气愤地狂笑起来,恶狠狠的笑声震得我正在溃烂的面颊发抖,而我疲惫痛苦的心脏中则注满了疯狂的仇恨。可这墙却依旧沉默着,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于是,那老妇人愤然挥动起干瘦蜡黄的双手,狠狠地痛骂道:
“你杀害了我的孩子,你必遭诅咒!”
潇洒、严肃的老头子重复着她的话,说:
“必遭诅咒!”
整个大地都重复着万民的咒骂声:
“你必遭诅咒!诅咒!诅咒!”
蒔岡雪子 · @Haruko
359 followers · 4320 posts · Server donotban.com人把墙视作朋友,紧紧地贴到它身上,把它当作靠山,求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墙却一直是我们的仇敌,一直是。我们的胆怯和畏缩使夜感到愤懑,它摇晃着阴沉沉的、斑污的大肚子,令人毛骨悚然地狞笑起来,苍老、荒秃的群山纷纷应和着这恶毒的笑声。幸灾乐祸的墙也欢乐地高声附和着夜的笑声,恶作剧般地向我们摔砖头取乐。砖头砸破了我们的头,打伤了我们的身体。它们,这些庞然大物,就这样此呼彼应、取乐自娱,那风还吹起野蛮的曲调,为它们伴奏。而我们呢,只好匍伏在地上,惊恐万状地谛听着地心深处那个巨大的东西怎样辗转翻滚,发出喑哑的怒吼,撞击着地心,要求把它释放出来、让它自由。这时,我们大家都祈祷着:
“杀了我们得啦!”
蒔岡雪子 · @Haruko
359 followers · 4320 posts · Server donotban.com我们是没有时间的,也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夜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黑沉沉的夜,竟也不到山背后去歇息歇息,以便精力充沛地、宁静地、黑得发亮地回来。因此它始终是倦怠的,令人窒息的,阴森森的。这夜可真是凶恶。它一听到我们的哀号和呻吟,看到我们在溃烂、痛苦和愤怒,就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它那黑乎乎的、默然起伏着的胸脯就因为暴怒而猛烈地摇晃起来。它变得像一头失去理智的困兽,朝着我们怒吼、狂叫,睁开眼睛怒视着我们,那恶狠狠的冒出火来的目光,把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傲慢地岿然不动的墙以及一小撮战战栗栗的可怜人照得通亮。
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
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我們向一扇窗子走過去。從房子的緊牆根開始,從屋簷板開始全是均勻的熊熊烈火般紅紅的天空,而且伸展到看不到邊的地方,沒有雲彩,沒有星星,也沒有太陽。而天空底下,則是同樣均勻的暗紅色的田野,地面上躺滿了屍體。所有這些屍體都一絲不掛,而且它們的腳都向著我們,因此我們看到的只是屍體的腳底板和三角形的下巴。而且還靜得很,——顯然,在這無邊無際的曠野裡,所有人,一個不漏地全死了......
“他們的數量在擴大。”哥哥說。
他也一樣站在窗子邊上,全家人都在這裡:母親、妹妹和所有這屋裡活著的人。他們的臉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憑嗓音聽出是誰來。
“這是一種感覺。”妹妹說了。
“不,是真實的。你看看。”
的確,屍體變得好像多了些。我們仔細地尋找原因,終於發現:一位死者旁邊原來空著的那塊地方突然出現了一具屍體:顯然是大地把它們扔出來的。所有空閒的地方很快被填滿了;接著,很快整個地面都因為躺滿蒼白和淡紅色的屍體而改變了顏色,這些屍體一排排躺著,赤裸的腳板對著我們。連房間裡也映射出這死亡的蒼白和淡紅的亮光。
“你們看,它們的地方不夠了。”哥哥說。
母親回答道:“有一個已經在這裡了。”
我們都轉過頭去看:背後的地板上已經躺著一具赤裸裸的蒼白和淡紅的屍體,它的腦袋向後仰著。它的旁邊隨即又出現了另一具和第三具。大地把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拋出來,於是所有房間很快被一排排整整齊齊的蒼白和淡紅色的屍體擠滿了。
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你們誰也不明白我寫的是什麼,你還笑我像個瘋子,可現在,我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你。我是在寫紅笑。你看見它了嗎?”
一種龐大的、紅紅的、血淋淋的東西出現在我面前,它的那張沒有牙齒的嘴在笑。
“這是紅笑。當大地失去理智的時候,它便開始這樣發笑。你是知道的,大地已經失去了理智。大地上沒有花,也沒有歌,它變得圓圓的、光滑的、紅紅的,像個剝了皮的腦袋。你看見它了?”
“是的,我看見了。它在笑。”
“你瞧瞧,它的腦子怎麼了。它紅紅的,像一團黏糊糊的血粥。”
“大地在叫喊。”
“它感到疼痛。它那裡既沒有花,也沒有歌。現在,讓我躺到你身上來。”
“我感到沉重,我感到害怕。”
“我們死人是躺在活人身上的。你覺得暖和嗎?”
“暖和。”
“你覺得好受嗎?”
“我要死了。”
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大地上彌漫著某種血霧,遮住了視線,於是我開始想,一場世界性的災難確實臨近了。是哥哥看到的那種紅笑。瘋狂是從鮮血染紅的戰場上產生出來的,我於是在空氣中感覺到了那紅笑的凜冽的呼吸。我是一個結實、堅強的人,沒有得使身體腐爛和導致大腦分裂的疾病,然而我發現傳染病正在侵蝕我,我的思想已經有一半不屬於我了。這比鼠疫及其造成的恐懼更糟。鼠疫,畢竟還是可以找個地方躲開的,在那裡採取一定的措施;而能穿透一切的思想,怎麼躲得了,它是多麼遠也隔不開、什麼障礙也阻擋不了的呀!
白天我還能進行鬥爭,可夜間就和大家一樣成了自己夢幻的奴隸;而且,我做的夢都是恐懼的和瘋狂的……
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MUZLT · @mushbuzz777
70 followers · 389 posts · Server m.cmx.im終於翻開買了很久的《撒旦日記》,挑了加略人猶大這一篇來看,愈看愈感受到安德烈耶夫的才華。猶大性格和長相並不討喜,一半瘋癲一半聰慧,大部分時候像個卑鄙小人,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通過他那些囈語似的自白漸漸感受到他對耶穌強烈的信仰和愛,故事中段門徒互相爭論誰才是最愛耶穌、最有資格第一個進入天國的人,猶大說是他自己,我還暗笑一聲,就你? 但讀到故事最後,卻產生了一種古怪的認同感,確實是他才有資格。
整篇故事給我的感覺也一如書封的顏色: 略為暗黯的紅,暴烈而矛盾,像是半乾涸的血,亦如陽光穿透緊閉眼簾達到眼球的紅。
「這顆腦袋被分成四個部份,令人無法信任甚至會引起不安,那樣一顆頭顱裡不可能有安寧與和諧,那樣一顆腦袋裡永遠回蕩着血腥而殘酷的爭鬥聲。」
「耶穌你現在相信我了吧? 我去你那裡。溫柔地迎接我吧,我累了。我會和你在一起,像兄弟一樣緊緊相擁,我們要重返人世,好不好......也許你還會為加略人猶大感到氣憤吧? 你不相信嗎? 要送我去地獄嗎? 我會下地獄的! 我會在你的地獄之火中鍛造鋼鐵,摧毀你的天堂。好不好呢? 那時候你就會相信我了吧? 那時候你就會帶我重返人世了吧?」